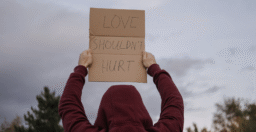洪一亘|永續青年檔案
台大社會一。熱愛社會學、人類學的精神。關心性別及性暴力、貧窮及無家者、教育議題。
活著的意義,是持續成為有能貢獻社會的自己:透過制度改革保障處境不利的群體,或透過學校教育、公眾倡議促進對話、帶動價值的變遷。
當某位男性被指控涉入性暴力事件,是否更常看到有人說「給他機會」、「別毀了他的未來」而非關注受害者的未來?當你看著主流電影、廣告或新聞,是否發現女性更常被強調外表及身材,而非能力或獨立?
你是否發現,當女性提出某想法卻被忽視,或常被男性插話、打斷而「耐心」地解釋她熟悉的概念?在捷運或公車上,你是否看過某位男性雙腿大開,使旁人只能縮著身體、帶來不舒適的乘坐體驗?
你覺得前述情境是小題大作,還是符合你的日常觀察?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和你的生理性別、社會性別、性別認同或性傾向有關。然而,若我們處在一個重視並持續實踐女性主義的社會,上述情境或許不會很常發生。因此,本文想和你分享「男性應瞭解女性主義的四個理由」。
1. 沒有置身事外的選項:女性主義和人人都有關
有些男性認為「女性主義只在乎女性的權益,我是男生,所以女性主義的事與我無關。」「我再怎麼努力,也找不到伴侶、找不到工作、賺不夠多錢,我們男性哪裡有特權?」「跟以前比起來,女性已經有了投票權、繼承權、工作權,選民代也有保障比例,哪裡不平等?」這些想法並沒有絕對的對錯,只是在觀點、立場和價值不同而已。然而,若我們習慣這樣思考,會喪失更深入瞭解議題的可能性。
一方面,支持女性主義與否是個人選擇的問題,無關身分。身而為人,我們擁有與社會中的成員互動的需求。凡是互動,必然接觸帶有不同身分、屬性、生活經驗的人,包含族群、階層、年齡、性別、性傾向、宗教信仰等等。因此,我們必然需要瞭解不同群體的人們的想法、感受、需求與困境,才能與之共處、更好地待人處事。若我們因為不具備什麼身分,所以不去管/去說/去做什麼,喪失和彼此對話、溝通的機會或可能性,我們將會迎來一個更為混亂、兩極、分化的社會。
另一方面,這忽略了性別權力結構如何影響整個社會。當男性順從既有的父權社會,即使個人在生活經驗中並沒有做出什麼侵害女性權益的言行,但男性確實在財產繼承、醫療照護體系、家務勞動、知識資格感、身體自主權、政治場域等面向享有特權(Kate Manne, 2021),也同時在過程中付出的額外的成本與代價(如後續我們將討論的情緒、人際網絡、家庭與勞動等面向)。
當我們認知到父權制和每個人都有關時,就能更瞭解女性主義的立場:多數的女性主義流派反對的不是男性,而是父權制(形成不平等的倫理道德、刻板印象、法律等等正式或非正式的規則)。即使是生理男性,也能「支持」女性主義(但生理男性是否能「成為」女性主義者是有爭議的,本文暫不處理)。
因此,一位男性為什麼願主動支持女性主義?因為他們與女性有具體的關係(妻子、情人、母親、姐妹、朋友、師長、工作夥伴等),並關心她們的福祉。因為男性群體內部有權力差異,因此他的朋友(不是阿法男,或不具備支配性的陽剛氣質/男子氣概等等)也在某方面受到體系的壓迫;因為男性擁有情感、希望及共感同理的能力,使他們能覺察結構、制度的問題,進而發現不平等、不合理之處,進而出於同理、良知而想做出改變。
2. 有毒的男子氣概:男性也被父權制綁架
許多男性常以壓抑的手段處理情緒。一種解釋來自於兒時在性別角色社會化過程中的負面經驗。如以下出自《該隱的封印》的內文:
「沒有外在的協助,本身也沒有適當的情緒裝備讓他脫困而出,許多男孩因此受困,將自己的情緒愈埋愈深,築起一道道堅固的門牆防止情緒流洩,一直到情緒被完全深鎖,再也無跡可尋。」
(Kindlon & Thompson, 2000: 213)
性別角色就是我們國高中公民課接觸到的性別刻板印象、性別偏見、性別歧視的相關內容。我們可以聯想,當男性從小被教導要堅強、負責任、不哭泣、獨立自主、賺錢養家、重視競爭、追求權力、不找人傾訴、追求他人肯認等等,未必能對男性帶來正面的影響。以下再舉兩例:
從人際網絡的層面來看,我們發現男性的狀態普遍較差:比較1997年與2017年的數據,男性的核心網絡(能提供較緊密的情感支持的人際互動)人數下降了將近2名,縮減的幅度(-43%)大於女性(-31%);當女性將朋友當成談心對象的比例提高,男性仍較少尋求心理支持,無人談心的比例也增加了27%(蘇國賢,2020: 86, 109)。
從家庭與勞動的層面來看,父權社會更是讓男性和女性都不好過:一方面,女性難以在和丈夫協商的過程中,在職場與家務之間取得平衡,因此要上第二輪班(the second shift),平均每年比男性多工作整整一個月。另一方面,男性被期待成為家中的經濟支柱,長時間工作、犧牲個人生活,在職場成為社畜,承受過大的競爭壓力(Hochschild, 2017)。
然而,為了「陽剛」而犧牲這麼多,值得嗎?男性有沒有權益選擇不同的人生,而不是被社會期待推著走?陽剛氣質的定義本身是多重的、動態變化的。從澳大利亞的女性主義社會學者R. W. Cornell的理論(2003: 105-109),我們可以從以下的兩組關係去討論陽剛氣質:
第一組是支配性、從屬性和共謀性陽剛氣質(hegemonic, subordinated, complicit masculinity)之間的關係。這描述整個社會如何建立一個標準,使不同性別的人各有需符合的期待。一方面,滿足期待的人擁有主導的地位,失敗的人則擁有從屬的地位。另一方面,有些人夾在中間:不僅對從屬者坐視不管,也倚靠霸權、享受父權制帶來的特權,便是共謀者。
第二組是邊緣性陽剛氣質(marginalized masculinity)和上述三者的關係。前述三者往往是變動的:在不同的互動情境、文化脈絡的協商與詮釋之中,你可能會擁有支配性、從屬性或共謀性陽剛氣質。邊緣性重視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的影響:一個人擁有的某些和性別看似無關的屬性(種族、階級、年齡),卻會和性別形成多重壓迫,進而加劇偏見、歧視。
我觀察到,生活中的許多男性先是處於從屬性或邊緣性的陽剛氣質,發展出較為不足的情感能力。接著,一部分男性透過支配性的陽剛氣質,透過憤怒、暴力、主導等手段去控制他人,但也有人將這樣的經驗壓抑至心中。
回顧以上,我相信,若能跳脫對支配性或共謀性陽剛氣質的追求、對從屬或邊緣性陽剛氣質的排斥,男性就不需要再逼迫自己扮演自己未必隨時都想扮演的角色。於是,男性若能跳脫社會對他的期待,他便能活得更自由。
3. 女性主義不是女生至上,而是性別平權
女性主義的流派十分多元,光是作為入門書的《女性主義理論與流變》就臚列了11種主要的流派,各派別的具體目標、主張、方法與論述都不盡相同。然而,女性主義理論仍有共同目標:
「一、分析男女不平等的現象,或女性的次等處境。二、以女性觀點解釋其原因。……。女性主義者著重於社會文化因素,使得改革顯得不僅可能,而且可欲。三、尋求改變。……。整體而言,女性主義可說是解構父權體制、建立新社會、新制度的思想工具與行動方案。」(顧燕翎,2000:4-5)
男性從小玩的就是充滿競爭意識的零和遊戲:不是你贏,就是我輸。因此,當某些男性聽到自由主義女性主義主張「讓女性擁有和男性一樣的權利」或後殖民女性主義主張「讓弱勢者獲得尊重」時,就認為其潛台詞是「要讓女性踩在男人身上」或「要讓女性和男性一樣擁有特權」。
然而,性別的遊戲不是零和的;我們擁有雙贏的可能性。在一個性別平權的社會,男性能過得比現在更好:在人際網絡方面,男性更能主動、積極、適時地找人傾訴,也建立更有品質、深度的人際連結;在家庭與勞動方面,男性能和子女建立更深厚的親子關係,女性取得事業成就也讓男性不用負擔這麼大的經濟壓力;在情緒方面,男性能練習覺察與表達,而不必總是壓抑或逞強。
因此,願意支持女性主義者的男性,代表他不認同壓迫女性的體制,而非認為所有男人都是壞人;代表他希望創造一個更公平的社會,而不是讓父權體制繼續剝奪人們的選擇權。支持女性主義,並不會「剝奪男性既有的權利」,而是「讓每個人都能獲得應有的尊重」。
4. 培養性別敏感度:避免厭女,是基本的尊重
什麼是性別敏感度呢?性別敏感度,是讓我們處理各種議題(勞動、階級、族群、軍事、科技、宗教、醫療、教育、健康等)時,都能帶入性別的視角(婦女研究、男性研究、酷兒研究等)。例如:我們能將性別視為一種結構,探討性別相關的概念如何在個體(individual)、互動(interactional)、組織制度(institutional)等層次或面向發揮作用(Risman, 2004)。
本段以厭女(misogyny)為例。什麼是厭女呢?根據專精於道德哲學、社會哲學與女性主義哲學的澳大利亞學者Kate Manne的定義:
「……我們不應該把厭女情結(misogyny)理解為一種對女孩和女人整體性的深層心理憎恨。相反的,要解釋厭女情結,最好的概念是把它想成父權秩序的『執法部門』──這個部門的功能是監管與執行性別化的規範和期待,讓橫跨不同年齡層的女性會因為性別與其他因素而遭受不合比例或格外具有敵意的對待。」Kate Manne, 2021
厭女的具體表現有很多:在某位女性因為性行為或性慾背離期待時,參與蕩婦羞辱(slut shaming);在性暴力事件發生時,責怪受害者的衣著暴露、言行不檢點、未積極反抗的強暴迷思(rape myth)。事實上,如前幾章所述,當男性未能遵照陽剛氣質的腳本演出時,他們也會受到懲罰與批評。例如:
「一個厭女的世界觀裡,在陽剛內部的階序中,女性的仰慕和贊同尤其賦予了男性相對於另一名男性的地位;當被拒絕或得不到這樣的注意力時,昔日的,或是有抱負的『阿法男』經常會病態地感到羞恥。」Kate Manne, 2017: 210
此處的阿法男(alpha man)指的是那些在群體展現強勢、領導、主導、果決、剛強、有主見等等形象的男性,符合我們前述描述的支配性陽剛氣質。可見,「女性的情緒或感受」似乎被轉換為一種可以被衡量、比較的「價值」,成為了男性彼此競爭的項目。
厭女的意義是複雜的,在每次互動的實踐過程中,厭女的意義被持續地創新、改寫而有不同的詮釋與內涵。然而,它的作用讓我們的理智受到蒙蔽,以為反對平權、維持現狀甚至支持父權就是最好的解方。於是我們將討論:在生活中,我們具體能如何做出改變呢?
5. 結論:我們可以選擇改變
首先,我們可以將女性主義的觀點主動應用生活、分析我們的經驗。還記得我們文章開頭舉的例子嗎?其實這些情境都可以透過女性主義的概念來提供更為清楚、明確、具體、全面的詮釋:
當社會對男性(尤其是性暴力加害者)過度同情,反而忽略女性受害者的痛苦與權益時,這則是種同理他心(Himpathy)。當男性以居高臨下的「你不懂吧,我告訴/考考你」的態度,向女性解釋她們熟知、甚至更專業的知識時,這是種男言之癮 / 男性說教(Mansplaining)。當男性在大眾運輸工具上佔據更多空間,造成他人的不便時,這是種男性開腿(Manspreading)。當媒體、廣告、電影習慣以異性戀男性的視角呈現女性,讓女性被物化為男性的觀看對象時,這便是種男性凝視(Male Gaze)。
其次,當我們在生活中能辨識出這些情境,我們就能在個體、互動、組織制度等層次或面向採取行動,帶來確實的影響力。例如:
當有人說「女生數理就是比較差」時,用數據說明,女性的數理成績整體而言優於男性;即使劣於男性,也很大程度是受到後天刻板印象的影響。當社群媒體的厭女言論百花齊放時,嘗試思考他為什麼能如此自信的這麼說?當朋友在互動中開物化女性、性騷擾的玩笑時,或許能問他「你要不要大聲地再說一次?」「你是否會和[某個他重視的人]這樣說?」讓他主動意識到這樣的說法可能有什麼問題(若他沒有意識到,就理直氣和的讓他意識到)。
討論至此,男性為什麼應瞭解女性主義?回顧本文:第一,我們沒有置身事外的選項:女性主義和人人都有關。在父權社會下,即使你想旁觀,也會在與人互動的過程影響他人與被影響。第二,男性跳脫陽剛氣質的束縛,活得更自由。從情緒、人際網絡、家庭與勞動的例子,我們看見一味追求或排斥陽剛氣質帶來的負面影響。第三,女性主義不是女生至上,而是性別平權。合作能破除對立,平權能帶來雙贏。最終,從厭女的例子我們看見,女性主義能帶領我們培養性別敏感度,以展現日常生活應有的基本尊重。
我相信,我們都曾被性別的框架綁架過。但請記得:我們可以選擇改變。性別平權不只是「女性的事」,它關係到所有人,包括你和我。當我們開始理解這些問題,我們才有機會創造一個更自由、更平權的社會。
參考文獻
Connell, R. W. (2003) 著,柳莉、張文霞、張美川、俞東、姚映然譯,〈男性氣質的社會組織〉,《男性氣質》,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Hochschild, A. (2017) 著,張正霖譯,《第二輪班:那些性別革命尚未完成的事》,2017,群學出版社。
Kindlon, D., & Thompson, M. (2000) 著,吳書榆譯,《該隱的封印:揭開男孩世界的殘忍文化》,商周出版。
Manne, K. (2019) 著,巫靜文譯,《不只是厭女:為什麼越「文明」的世界,厭女的力量越強大?拆解當今最精密的父權敘事》,麥田出版社。
Manne, K. (2021) 著,巫靜文譯,《厭女的資格:父權體制如何形塑出理所當然的不正義?》,麥田出版社。
Risman, Barbara J. “Gender as a Social Structure: Theory Wrestling with Activism.” Gender and Society, vol. 18, no. 4, 2004, pp. 429–50.
蘇國賢著,〈臺灣個人核心網絡的變化:比較1997 年與2017年的差異〉,《臺灣社會學刊》,第67期,2020年6月,頁63-134。
顧燕翎主編(2020),顧燕翎、劉毓秀、王瑞香、林津如、范情、張小虹、黃淑玲、莊子秀、鄭至慧、鄭美里著,《女性主義理論與流變》,貓頭鷹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