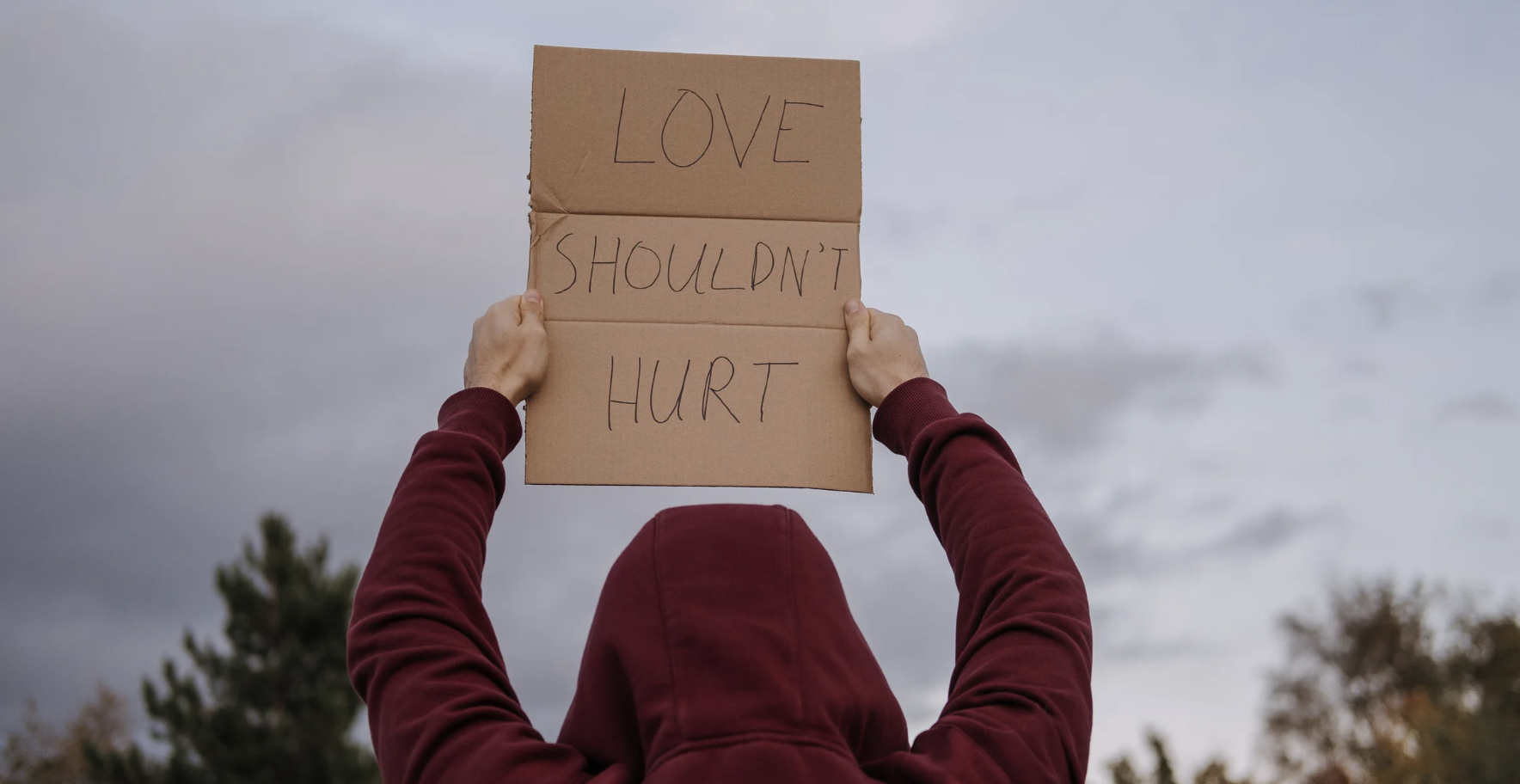洪一亘|永續青年檔案
台大社會一。熱愛社會學、人類學的精神。關心性別及性暴力、貧窮及無家者、教育議題。
活著的意義,是持續成為有能貢獻社會的自己:透過制度改革保障處境不利的群體,或透過學校教育、公眾倡議促進對話、帶動價值的變遷。
「我被性侵了。」
若有一天,你的男性友人、伴侶、同學、兄弟、父親、孩子、叔叔、伯伯、舅舅或姪子這樣和你說,你會做何反應?
你會感到半信半疑,詢問事件發生的細節嗎?還是手足無措,語塞尷尬,嘗試轉移話題呢?還是覺得他很勇敢,但不知道怎麼辦、如何接住他?甚至,相較多數的女性受害者,他受的苦沒那麼多,也沒有創傷可言,對吧?
2013年,《如果早知道男生也會被性侵》由國家教育研究院推出,因主角杰哥和阿瑋的逼真演技與迷因台詞而蔚為風行。這或許讓我們瞭解「男生也會被性侵」的觀念。但你是否想過,性暴力受害者有多少比例是男性?男性受害者在發聲、求助的過程中,又會遇到哪些困境?
根據衛福部對2024年性侵害案件的統計,所有受害者有超過一半是未成年兒少。其中,所有受害者的男女約為9:1,兒少受害者的男女比約為3:1。我們不妨從一個問題開始:什麼樣的人,才會被社會認為是「真的」受害者?當那個人是男性時,事情又會變得多麼複雜且困難?
更難發聲的男性受害者
我們先討論延遲求助的問題。首先,什麼是「求助」呢?所謂的「求助」或「揭露」包含正式與非正式的管道,前者包含醫院、檢警、校方、公司等機構,後者則包含家人、朋友、伴侶等管道。重要的是,相較正式管道,性侵害倖存者傾向透過非正式管道求助(王麗容、黃冠儒2021:63)。綜合上述原因,相較其他犯罪,性侵害的正式通報黑數極高。
接著,「延遲」的現況是什麼呢?根據香港風雨蘭(2022),兒少受害者平均延遲12.8年求助,為成人性侵害個案的10倍以上。又根據澳洲皇家調查委員會(2017),兒少平均延遲23.9年,其中男性平均延遲31年,女性延遲21年。換句話說,許多男孩直到步入中年,才第一次說出童年的傷痛。加上前述衛福部的統計,男性相較女性、兒少相較成人面臨更嚴重的延遲求助問題。
延遲求助帶來的後果是什麼呢?最直接的影響是倖存者長期所受的身心折磨,但更危殆的是受害者的求助將受阻。在法律上,「插入」行為並非性侵害的充分條件;猥褻、性交都是性侵,皆屬於妨害性自主罪。當受害者願發聲、想進入正式體系求助時,很容易發現:刑事追訴期之時效已過,追訴權已消滅。
具體來說,根據我國刑法第80、221-1和224條,我國的強制猥褻罪、強制性交罪的法律追溯期原則上分別是20年、30年。然而,強制性交罪的法律追溯期在2006年修法前是20年。根據從舊原則,今日若針對事發於2006年以前的性侵害提告,強制性交罪的法律追溯期仍會以20年計算,難以因應性暴力兒少受害者的處境(這成為近年許多性別倡議團體爭取釋憲的原因之一)。
避免加劇女性困境的男性受害者
由上可見,延遲求助的問題是普遍存在的。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可以追問的是:性暴力受害者的發聲為什麼充滿障礙呢?整理學者王麗容、黃冠儒(2021)與自由撰稿人陳昭如(2022)的觀點,受害者未通報的原因包含:
1、不清楚性侵害的定義,常自問「這算不算性侵?」而難以形成求助的動機。2、事發當下未能存證,例如透過驗傷採證的體液、汗水、皮屑等等,自認證據不足。3、畏於承擔「沒人信任自己」的風險。4、擔心會讓信任自己的朋友、家人比自己還痛苦。5、身體因自我保護而遺忘事件帶來的感受,因此在偵查、審判等階段難以清楚描述傷害。6、和加害人的權力不對稱,擔心遭報復。7、不信任檢警系統,例如怕被問「你為什麼沒反抗?」使自己被譴責。8、偵查階段不起訴或審判階段敗訴的比例很高,此結果易帶來二次傷害。
上述是不分性別皆可能阻礙受害者發聲的原因。不過,男性為什麼更難以發聲呢?首先,男性受害者的經驗難以被某些國際組織或政府正視。Bourke(2025: 134)引述其他組織的觀點提到「同時報導男性和女性遭受的強暴行為是個『零和遊戲』。」所謂的零和遊戲(zero-sum game),就是要嘛你贏我輸、要嘛你輸我贏,沒有雙贏的選項。
這反映部分學者的觀念:全體男性是潛在的加害人,全體女性是潛在的被害人,性暴力就是MacKinnon主張的「男性對女性的統治」。甚至有組織主張「如果向男性性虐受害者提供協助與支持,恐怕會侵蝕女性受害者享有的珍貴資源(轉引自Bourke 2025: 134)。」換句話說,當男性加害者、女性受害者的比例總是佔絕對多數,我們似乎就要對其他的可能性視而不見。
此外,我認為延遲求助的主因是「完美受害者」與「陽剛氣質」的矛盾。想像一下,你是生理男性,從八歲起的每年暑假,因應父母雙薪工作,你被託給表舅照顧。表舅除了照顧你的起居之外,卻不時撫弄你的身體、要求你觸摸他指定的部位。當你意識到這是性暴力的時候,三年過去了。
長年下來,你敢求助嗎?敢或不敢的原因是什麼呢?除了前述的性別組織的因素,我們想從「完美受害者」的角度來邀請你一起思考。
污名作為一種受損的社會身分
我認為=性暴力受害者」是種污名,即「受損的社會身分」。什麼是社會身分呢?社會身分由分類和屬性組成。其中,分類是「我是哪類人?」像是性別、職業、種族等身分認同。屬性則是「依照分類,我應該是什麼樣的人?」像是堅強、積極反抗等特質。於是,在日常社會互動的各種情境中,分類讓社會識別我們是誰,屬性則讓社會評價我們是否值得被信任、幫助與理解。
那社會身分具體如何運作呢?Goffman(1963)區分了虛擬社會身分(virtual social identity)與實質社會身分(actual social identity)。這樣區分,是因為一個人的理想與現實身分,總會有落差。正如他人未必滿足我們對他的期待,而我們也未能總是滿足社會對我們的期待。接著,當落差出現,污名便產生:我們不再被視為健全、正常或道德的人,我們的社會身分也因此受損了。
當我們提到性暴力受害者時,你通常會聯想到哪些特質?在媒體報導、法庭判例等等管道建立的敘事中,被害人通常是位順性別異性戀女性,平日端莊寡欲、極少和人發生性行為,遭遇性暴力時能積極抵抗、及時蒐證,事後立即驗傷、報案,並在求助的過程全然配合,毫無矛盾、遲疑或痛苦地訴說事件經過。這些倖存者被期待擁有的特質,形成完美被害人的虛擬社會身分。
當我們提到男性時,你又會聯想到哪些屬性呢?顯然的,在家庭、學校、同儕、傳播媒體等管道的耳濡目染下,一個男性應該是順性別、異性戀,從小則被教導要堅強、負責任、不哭泣、獨立自主、積極競爭、追求權力等等。這些陽剛氣質或男子氣概的內容,構成了男性的虛擬社會身分。
但我們需留意的是,當社會形塑任一種虛擬社會身分的同時,社會也排除了其他身分存在的可能性。換句話說,任何分類似乎都有它理應具備的屬性,而且這樣的屬性是單一的、固定的、值得追求的。這帶來什麼後果呢?這會窄化我們對某個群體的理解,忽略群體內部的多樣性。
陽剛氣質和完美受害者衝突的男性受害者
當男性說出「我被性侵」時,他們往往缺乏所謂的「完美受害者」的特徵,既少被媒體正視,也難被法庭相信,最終被排除在輿論的同理與司法的正義之外。以下從不同方面論述「陽剛氣質」和「完美受害者」的矛盾。
在性格特質方面,男性的虛擬社會身分應是堅強的、有支配力的主體,但性暴力受害者的虛擬社會身分常是脆弱的、無力的。當男性受害者表現得太懦弱,會被認為不像男人而不值得被同理。若表現得太堅強,則會被懷疑性侵害事件是否發生,或是帶來的傷害有限。甚至,他若在被性虐待的過程產生性興奮的反應,還會被質疑是否「潛意識的想要」(Bourke 2025: 144)。
在性傾向方面,男性的困境和恐同(同性戀恐懼)的心態有密切的關係。例如:如果一個異性戀男性被性侵,他可能擔心自己變成同性戀,也害怕自己在發聲的過程被他人當作同性戀;如果一個非異性戀被性侵,他可能誤將性侵害的後果歸因於自己的性傾向,或是因此企圖改變、矯正自己的性傾向。我們可以留意的是,很少有異性戀受害者把性侵害歸因於自己的性傾向。
在社會化的角度來看,男性的社會互動經驗不乏性嬉戲,例如阿魯巴、猴子偷桃等等以暴力方式戲謔同性下體的校園玩笑。於是,「以男性的生殖器官與生殖系統為目標的暴力,往往以無性的方式加以歸類(Bourke 2025: 135)。」換句話說,同樣的行為對女性施加若被視為「性暴力」或「性傷害」,對男性施加時可能只被視為「暴力」或「一般傷害」。這使男性更難以辨識自己遭受言行是否屬於性暴力,也使男性承受的性暴力經驗被嚴重低估。
這正是Goffman所描述的污名機制:男性性暴力倖存者不僅在訴說創傷,更在承擔一種身分上的撕裂。他們的經驗,既需要打破「男人難以被性侵」的迷思,也需動搖「好受害者才值得被相信」的邏輯。
結論:羞恥必須轉向
在文章開頭,我們透過性暴力受害者的數據以說明延遲求助的現況。然而,重要的不只是數字本身,而是數字背後的每個說不出口的故事。
我們要記得,說不出口的原因,來自於社會建構的污名,而非個人的缺陷;來自社會不合理的預設與分類標準,而非無法滿足大眾期待的倖存者。一個完美受害者,會拒絕那些不符預期的人,會疏遠那些歷經創傷的人;會迫使倖存者持續沉默,會讓結構性的性暴力問題難以被正視與解決。
那麼,我們能做什麼?我們理解與支持所有性暴力倖存者的第一步,是意識到「羞恥必須轉向。」這句“Shame must change sides.”是性暴力受害者吉賽兒‧佩利寇(Gisèle Pélicot)於2024年對大眾發出的呼籲:該承受污名的不應是受害者,而應是加害者。
面對生活中潛在的倖存者,我們也不必要求他們應做些什麼。原諒的結果值得被讚許,但不值得被強迫。正如台灣著名男性受害者陳潔皓提到,「我想過我平靜的生活,我有我愛的人,我有朋友,有信心我能療癒我自己,我不需要去符合這社會無理的期待去原諒、包容一個加害人(2016:146)。」
當我們拆解「完美受害者」與「陽剛氣質」的敘事,我們才能打破無形的審判之牆;當我們認知到社會身分是建構的而非本質的,例如從性格特質、性傾向、社會化等面向來思考,我們才能讓每種倖存的方式都盡力被傾聽、被理解。最終,我們才能更接近一個人人不需擔憂自己遭遇性暴力的社會。
參考書目
Bourke, Joanna. 2025,陳信宏譯,《恥辱:一部性暴力的全球史》。台北:衛城出版。(_. 2023. Disgrace: Global Reflections on Sexual Violenc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17. “Preface and executive summary,” in 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Final Report. p.23. https://ppt.cc/fBgCwx
Goffman, Erving. 1963.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王麗容、黃冠儒。2021。《大專院校學生性侵害受害經驗調查:心理影響、求助行為與體制背叛感》。教育心理學報,53(1):61–84。
陳潔皓。2016。《不再沉默》。台北:寶瓶文化。
陳昭如。2022。《判決的艱難:兒童性侵的爭議與正義》。台北:春山出版。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2022/3/8。〈「風雨蘭」去年跟進逾千宗性侵個案 受害兒童平均事隔逾十年方求助〉。https://ppt.cc/fRp8Mx
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2024/6/12。〈性侵害案件被害人年齡與性別交叉統計〉。https://ppt.cc/f4qVwx